
兴教寺修复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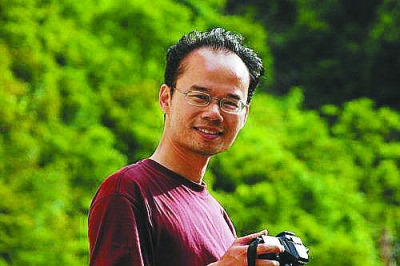
黄印武
□人走了,人来了,人又走了——黄印武在沙溪看到过3次村民的迁徙。在这个“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他一待就是12年。
□随着古镇的修复,他预想中让本地人过上更好生活的目标似乎并没有实现。人们选择把房子租给外地人,自己搬到更远的地方盖新房。现在的寺登村已经离黄印武最初的理想越来越远了。
□很多人担心它未来的命运: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丽江,或者一片旅游文化商业的热土?
人走了,人来了,人又走了——黄印武在沙溪看到过3次村民的迁徙。
2003年,带着国外的资金和年轻人的固执,建筑师黄印武最初来到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沙溪镇寺登村。在这个“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他一待就是12年。
起初,他是一名尊重历史的古建筑修复者,后来,他做的事情离建筑越来越远,更像一名乡村建设者。
古建修复的成功犹如打开了一幅边陲秘境的寂静画卷,暴富的客栈老板、酒吧爱好者、咖啡馆投资商,欲望膨胀的本地人、野心勃勃的管理者,各色人等陆续亮相。
当寺登村的发展脱离了服务当地人的轨道,黄印武开始思考行之有效的乡村建设道路。那既不是对城市的拙劣模仿,也并非对乡愁的浪漫想象。
“沙溪不是摆在博物馆里展览的器物,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一草一木、它托举的日常生活以及发生在其上的故事,这些‘活的东西’全都是保护的对象”
沙溪给黄印武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人烟稀少。当这个戴着眼镜、头发稀疏,散发着学者气息的建筑师来到沙溪时,一切都像门口贴着的对联一样在褪色——木制的门窗看上去摇摇欲坠,房前屋后堆着破砖烂瓦,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外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专员杜晓帆也曾在那时来过沙溪,看了这幅景象,嘴里一直重复着“怎么办,怎么办”。
沙溪北靠藏区,南面是普洱茶的产地,茶马古道因此经过沙溪。这里曾经商贾游客云集,三教九流汇聚。自此,小镇的命运系在交通工具迭代的历史中。
自上世纪50年代,汽车的脉搏切分着镇子的时间与日常。马帮不再荣耀,茶马古道逐渐衰落,沙溪又重新回归了宁静,“躲”在群山中,一待就是50年。
当载着黄印武的吉普车第一次开进沙溪时,黄印武回忆,“感觉像是穿越了”。
那时,黄印武刚刚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学成归来,在这里主导设计和实施工作。瑞方希望在茶马古道上复制自己成功的古建修复模式,于是选中了沙溪,有了“沙溪村落复兴工程”项目。整个项目由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主持,世界纪念建筑基金会筹措慈善资金,“试图通过对当地村落文化遗产、生态景观的保护,实现对当地村落经济的脱贫和文化传承”。
那时,除了黄印武代表的瑞方,似乎没有人确切地明白“沙溪村落复兴工程”真正的涵义。在黄印武看来,沙溪复兴中的古建保护,并非单纯的建筑修复,而是文化自信心的重建。当村民的信心恢复以后,村子的发展才会有自主性,而非盲目追随别人的道路。黄印武以为,等村子修复了,人,迟早会回来。
在黄印武刚到县城剑川,还没来得及下到镇里时,县里的领导就拍着胸脯说:“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建筑,把想法拿出来,我们的工匠都能做到。”
彼时的黄印武带着书生气,是个靠谱的执行者,接到瑞方的电话,总是回答yes,yes,yes,以至于施工队的工人开玩笑说,打英语电话其实很简单,只要回答yes就可以了。但他对县政府的说法还是充满了警惕:“他们以为这是个‘体力活’。”只要修出来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建筑就行了,管它是新还是旧。
在黄印武看来,“沙溪不是摆在博物馆里展览的器物,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一草一木、它托举的日常生活以及发生在其上的故事,这些‘活的东西’全都是保护的对象”。所以那些拆了旧建筑,号称造出一件“一模一样”的新建筑的做法,在他看来十分简单粗暴。怎么可能一模一样呢?老建筑上的一个“疤”,背后可能上演过一段传奇往事;每一块木头都能成为后人工具研究的证物——比如这是用斧头凿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刨子。
当时的项目组不足十人,由瑞方和县里抽调来的工作人员组成。最忙碌时,要统筹200人施工。杨爱华来到项目组时刚刚20岁出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在施工队后面,记录下他们拆下哪块瓦、哪块砖,给它们编号,再重新放回原处。
(责任编辑 :徐晶慧)